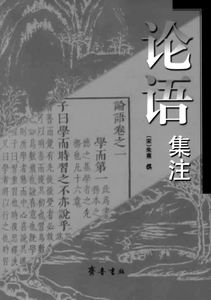 这是《论语》首篇《学而》的第一章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,特别展示了此章中的
这是《论语》首篇《学而》的第一章。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,特别展示了此章中的
《论语》各篇在排序上似乎并没有深味可寻,但古人重始。孔子留下的语录那么多,为什么选这一条作为全书的开始,这却不能说是没有用意的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谈到《学而》篇时,曾指出:“此为书之首篇,故所记多务本之意,乃入道之门、积德之基、学者之先务也。”朱熹说的是《论语》首篇,不是首章。这一章之所以被编撰《论语》的孔门弟子作为全书的首章,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孔子一生的理想与成就、遭际与境界,适合作为理解全书的枢纽。
“学而时习之”之“说”并非是单纯强调温故之乐。孔子之前,“学”是“官学”,为官府所垄断、世袭,“官”以外几乎无学。到孔子时,礼崩乐坏,学在四夷,孔子亦始办私学。虽说由此造成学术下移民间,但治学与从政的关系并没有断。朱熹《论语集注》引程子曰:“学者,将以行之也。时习之,则所学者在我,故说。”这个分析包含两层意思:一是说,“学”是为了学以致用,“行之”用孔门的话说,也就是“学干禄”,或者说“学而优则仕”;一是说,通过不断温故知新,已经“学者在我”,掌握天道人文之理,学有所成,所以“说”,值得高兴。
“有朋自远方来”,“有朋”古本或作“友朋”。这里的“友朋”,并不是指今日意义上的朋友而言。在孔子那个时代,“士”作为底层贵族有招募“朋友”作为自己从属来辅佐自己从政的礼度。《左传》襄公十四年,晋国师旷尝谓:“天子有公,诸侯有卿,卿置侧室,大夫有贰宗,士有朋友,……皆有亲昵,以相辅佐也。善则赏之,过则匡之,患则救之,失则革之。自王以下,各有父兄子弟,以补察其政。”《左传》桓公二年,晋大夫师服谈到周代的贵族制度,曾说:“天子建国,诸侯立家,卿置侧室,大夫有贰宗,士有隶子弟”。两相对照,一般认为师旷所谓“士有朋友”就是师服所说的“士有隶子弟”。这些“子弟”和“士”并没有什么血缘关系,但他们归附在“士”的周围辅佐“士”,被“士”待如父兄子弟,帮助“士”“补察其政”。
就孔子来说,孔子的身份基本上属于贵族中的“士”。据《孔子家语・本姓解》及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所言,孔子之先,本为宋之世卿,后流亡入鲁,且最迟至孔防叔之时其爵已沦落为“士”。所以《本姓解》载颜氏之言,于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有“虽父祖为士,然其先圣王之裔”云云。《论语・子罕篇》载孔子亦有“吾少也贱”之叹。《孔子世家》虽说孔子中年仕鲁而官至大司寇,《论语・宪问篇》又说他晚年返鲁位“从大夫”之后,然而就孔子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来说,其实际爵位依然是属于“士”这一阶层。为什么这样说呢?《礼记・王制》云:“大夫废其事,终身不仕,死以士礼葬。”孔颖达疏引《论语》郑玄注曰:“大夫退死,葬以士礼;致仕,以大夫礼葬。”也就是说,大夫居其位则为大夫,年老致仕亦爵如大夫;退避则不然,退避则爵降为士。故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・子罕篇》云:“夫子仕鲁为司寇,是大夫也。及去鲁,以微罪行,宜降用士礼。”(《论语正义》,中华书局1990年版,P142)《孔子世家》中,太史公说“孔子布衣,传十余世”,曰孔子为布衣者,盖即以此也。
就孔子的学生来说,他们既经常被孔子称为“朋友”,也经常被孔子待为“子弟”。《尚书大传》卷二载:
文王胥附、奔辏、先后、御辱谓之四邻,以免乎牖里之害。懿子曰:“夫子亦有四邻乎?”孔子曰:“文王得四臣,吾亦得四友。自吾得回也,门人加亲,是非胥附邪?自吾得赐也,远方之士至,是非奔辏邪?自吾得师也,前有辉,后有光,是非先后邪?自吾得由也,恶言不至于门,是非御侮邪?文王有四臣以免虎口,丘亦有四友以御侮。”(伏生:《尚书大传》,嘉庆庚申爱日草庐藏本,卷二,P4下)
 《尚书大传》所记孔子之事,又见于《孔丛子・论书》而文字略有不同。在这一记载中,孔子不但将四个弟子颜回、子贡、子张与子路称作他的“四友”,而且将四人比作辅佐周文王的“四邻”,由此可见孔子与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主从关系,并非只是普通的师生而已。孔子应当就是被辅佐的“士”,而他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被看作是他的“朋友”。他们前来依附他并辅佐他。按照师旷所言,“朋友”对于“士”的辅佐具体表现为“善则赏之,过则匡之,患则救之,失则革之”,而孔子的许多学生事实上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辅佐孔子的。如《论语・阳货篇》载,公山弗扰以费叛鲁,召孔子,孔子欲往而为子路所阻;佛?以中牟抗赵简子,召孔子,孔子欲往而又为子路所阻,即所谓“过则匡之”。又据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,孔子罹难于蒲,其弟子公良孺奋死与蒲人斗,即所谓“患则救之”。这样的事例还很多,足以说明孔子与其部分学生的关系符合师旷对“士有朋友”涵义的阐述。同时也说明,“士有朋友”之“朋友”并非今日一般涵义上的朋友,而是对“士”具有辅佐义务的仆从,亦即当时人所谓之“隶子弟”。孔子不但将其部分学生称作“朋友”,而且也常待之以宗族子弟之礼。《礼记・檀弓上》载:“孔子之丧,门人疑所服。子贡曰:‘昔者夫子之丧颜渊,若丧子而无服,丧子路亦然。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。’”由此可见,子路、颜渊这两个“朋友”,还被孔子在丧服上待若宗族子弟。再者,就《论语》一书来看,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兴办私学的人,孔子经常称他的学生为“弟子”。如《雍也篇》载哀公问“弟子孰为好学”,孔子对以颜渊。《先进篇》载季康子问“弟子孰为好学”,孔子又对以颜渊。孔子为什么称其学生为“弟子”呢?以当时礼法来看,孔子与其学生实属“士”与其“隶子弟”之关系。
《尚书大传》所记孔子之事,又见于《孔丛子・论书》而文字略有不同。在这一记载中,孔子不但将四个弟子颜回、子贡、子张与子路称作他的“四友”,而且将四人比作辅佐周文王的“四邻”,由此可见孔子与这些学生具有一定的主从关系,并非只是普通的师生而已。孔子应当就是被辅佐的“士”,而他的学生至少有一部分应当被看作是他的“朋友”。他们前来依附他并辅佐他。按照师旷所言,“朋友”对于“士”的辅佐具体表现为“善则赏之,过则匡之,患则救之,失则革之”,而孔子的许多学生事实上也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来辅佐孔子的。如《论语・阳货篇》载,公山弗扰以费叛鲁,召孔子,孔子欲往而为子路所阻;佛?以中牟抗赵简子,召孔子,孔子欲往而又为子路所阻,即所谓“过则匡之”。又据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,孔子罹难于蒲,其弟子公良孺奋死与蒲人斗,即所谓“患则救之”。这样的事例还很多,足以说明孔子与其部分学生的关系符合师旷对“士有朋友”涵义的阐述。同时也说明,“士有朋友”之“朋友”并非今日一般涵义上的朋友,而是对“士”具有辅佐义务的仆从,亦即当时人所谓之“隶子弟”。孔子不但将其部分学生称作“朋友”,而且也常待之以宗族子弟之礼。《礼记・檀弓上》载:“孔子之丧,门人疑所服。子贡曰:‘昔者夫子之丧颜渊,若丧子而无服,丧子路亦然。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。’”由此可见,子路、颜渊这两个“朋友”,还被孔子在丧服上待若宗族子弟。再者,就《论语》一书来看,作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力兴办私学的人,孔子经常称他的学生为“弟子”。如《雍也篇》载哀公问“弟子孰为好学”,孔子对以颜渊。《先进篇》载季康子问“弟子孰为好学”,孔子又对以颜渊。孔子为什么称其学生为“弟子”呢?以当时礼法来看,孔子与其学生实属“士”与其“隶子弟”之关系。
孔子与其门人这一层关系及其内涵,后人多不甚了了。程子曾将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理解为:“以善及人,而信从者众,故可乐。”程子不了解“朋友”的古义,不知道孔子的这些弟子、朋友对孔子有“善则赏之,过则匡之,患则救之,失则革之”的责任,以为孔子之所“乐”在于“信从者众”。“信从者众”固然是可“乐”的,但对于孔子来说,更值得高兴的恐怕更在于这些弟子可以帮助他匡救过失,切磋道义。我们来看载诸《论语》的夫子之言:
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?孔子曰:“知礼。”孔子退,揖巫马期而进之,曰:“吾闻君子不党,君子亦党乎?君取于吴为同姓,谓之吴孟子。君而知礼,孰不知礼?”巫马期以告。子曰:“丘也幸,苟有过,人必知之。”(《述而》)
子曰:“回也非助我者也,于吾言无所不说。”(《先进》)
孔子曰:“益者三友,损者三友。友直,友谅,友多闻,益矣。友便辟,友善柔,友便佞,损矣。”(《季氏》)
据这些记载,孔子显然是一个要求朋友能够对其过失直言规谏并以此为乐的人。又如《论语・八佾》载:
子夏问曰:“‘巧笑倩兮,美目盼兮,素以为绚兮。’何谓也?”子曰:“绘事后素。”曰:“礼后乎?”子曰:“起予者商也!始可与言诗已矣。”
孔子对子夏能够“起予”是多么的开心和愉悦。这不正是“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”的一个具体表现吗?联系上一“说”,此一“乐”应是说孔子习知天道人文之后,得到很多人的拥护,愿意与他一起去如切如磋,共同致力于弘扬天道,所以值得一乐。
“人不知而不愠”,汉魏旧注以为“凡人有所不知,君子不怒”。这个说法没有对“人不知”作具体解释。刘宝楠《论语正义》说:“‘人不知’者,谓当时君卿大夫不知己学有成举用之也。”这个解释比较流行,有商榷的地方。因为孔子周游列国不得重用,并不是各国君卿认为他学未成,情况恰恰是相反的。据司马迁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,孔子在齐不得任用,是因为晏婴认为孔子之学不适合齐国国情。其后孔子归国,以大司寇摄相事,国家大治,齐人闻而惧,曰“孔子为政必霸”,可见齐人也认为孔子是学有所成。再如《史记》载:
昭王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。楚令尹子西曰:“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?”曰:“无有。”“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?”曰:“无有。”“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?”曰:“无有。”“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?”曰:“无有。”“且楚之祖封于周,号为子男五十里。今孔丘述三五之法,明周召之业,王若用之,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?夫文王在丰,武王在镐,百里之君卒王天下。今孔丘得据土壤,贤弟子为佐,非楚之福也。”昭王乃止。
这一记载最足证明孔子不得仕,并非人不知其有学,而恰在于人知其有学,而且又知其能得众,有众贤弟子相佐。
《荀子・法行》载:
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:“夫子之门何其杂也?”子贡曰:“君子正身以俟,欲来者不距,欲去者不止。且夫良医之门多病人,?栝之侧多枉木,是以杂也。”
《论语・述而》载,子曰:“自行束修以上,吾未尝无诲焉。”《论语・卫灵公》载,子曰:“有教无类。”可见孔子招收门徒弟子,是不拘一格,来者不拒的。这种态度在今日看来是好的,但在当时,从《荀子》的记载来看,孔子却不太被人理解。联系上一句“有朋自远方来”,“人不知而不愠”的“不知”也许更可能是指孔子所招弟子门人品类过于驳杂,故而不为时人所理解。孔子的这一做法虽不受时人理解,但是对于那些出身卑贱、受人歧视而却得到孔子不倦教诲的弟子们来说,还有什么比老师的这一思想更值得珍爱、更值得感激的呢?出于这种切身的感受,在书的首章首列夫子坚持教无类、为此遭人误解也无所怨的言论,岂不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吗?更何况,在孔子这一夫子自道中,既显示了孔子学优得众的人生成就,也表现了孔子不被世俗理解犹能坚持真理、积极用世的高贵品格,因而将其置于全书之首用来引领人们去阅读《论语》,体会夫子之美,难道不是再合适不过的吗?!
